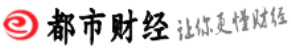深圳前副市长:研究了7000家企业5年的数据,发现“深圳奇迹”诞生的秘密
2020-10-15 15:17:16
深圳需要從創新制造走向科學發現。 ——唐傑

唐傑教授 4 月 20 日在《深圳奇蹟》新書首發式上的演講
我比較贊成海聞(編者注: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剛纔說的那句話:“社會科學也是科學”,所以也需要支持,深圳缺乏社會科學,深圳的社會科學相對於理工科是落後的,我想這是深圳奇蹟及未來應該要討論的東西。所以首先要祝賀張軍教授,長期在深圳可能就看不清楚,第三隻眼睛才能看清楚。

40 年,圖片(編者注:深圳今昔對比圖)是最經典的,世界上沒有一座城市能夠有深圳這樣 40 年的滄桑鉅變。當然,有一個城市比深圳富得快,那就是迪拜。它比深圳晚開發 10 年,它現在比深圳富。但它沒有經歷過一個完整的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我們也應該佩服阿拉伯人,在一個沙漠中,建起了一座繁華的城市,但是它和深圳具有巨大的差別。

這兩個鏡頭大家都知道,一張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一張是通過經濟特區報告的會審。李嵐清寫出過一段史實,小平當年有段話,“就叫特區,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中央只給政策不給錢,你們殺出一條血路來”。當時都不清楚這個話從哪兒來,因爲沒頭沒尾嘛。後來知道那是兩個老人家聊天,一位是做過陝甘寧邊區領導人的,當年國民政府是不給陝甘寧邊區錢的,那麼另一位老人說,中央也不給你錢,你們殺出一條血路來。深圳真正走到今天就是改革開放闖出來的。我們現在很多地方講四平八穩,確保萬無一失。沒有這個事,改革就是要有風險。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組擺在深圳博物館的照片,白天工作,晚上學習,照片上是同一位女工。我覺得這是深圳 40 年能夠走到今天的寫照,一個城市學習的過程。
我想說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學科對深圳現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很多人將其歸功於深圳是移民城市,爲什麼移民城市能成功?社會學解釋比經濟學解釋更好,社會是分層的,一個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層,我們很難想象復旦經濟學院的院長和一個普通工人能坐在一起討論創新。但是在深圳就可以,因爲大家都是移民,這兩人可能是老鄉,可能是戰友,雖然你現在當院長,但是咱們還可以以同學、同鄉或者戰友的名義聚在一塊。老的城市很難創新的原因就是社會分層嚴重,不同路徑、不同思想的人很難在一起碰撞。深圳著名的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就給大家創造了一個交流的平臺,在這個交流當中可能就有三種人,一個是當過兵可以管人的,一個是科學家有技術的,一種是有錢的,再一個是在政府當過處長的,四個人聚一塊這個企業可能就出來了。深圳的野蠻生長、草根生長,這是一種城市化中的社會學現象。
再一個科學學角度的解釋,我們不知道誰能得諾貝爾獎,但是我們知道諾貝爾獎的科學發展是有規律的,所以我們就知道世界上曾經組織大科學計劃最成功的是美國。美國做原子彈開發引導世界走向了核時代,登月計劃引導世界走向宇航時代,組織 10 個國家 100 個科學家 10 年花了 37 億美元做了人類第一張基因圖譜,使人類走向生命科學、基因的時代。所以從科技學角度來講,對深圳最大的啓發是配齊產業鏈。深圳政府最愛乾的事就是研究產業鏈,不說誰能夠在產業鏈中承擔一個份額,但是我知道缺了這個東西做不成。

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學能夠解釋深圳的什麼呢?
首先經濟學解釋激勵,創新創業就會有激勵,爲什麼很多城市不能創新創業?因爲沒激勵,創不成,等你創成了一個東西,簡單就被別人抄襲走了,你打官司打不贏,沒處打。有一個激勵機制之後,就會變成一個創新效應、示範效應,變成在深圳由一個任正非帶動無數人想當任正非。
但是經濟學不能解釋什麼呢?經濟學不知道誰能成爲企業家,海校長(編者注:海聞)說北大匯豐是商界領袖的搖籃,但他沒說是企業家的搖籃,他很難說誰能當企業家,反正我知道我當不了,我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有人要來讀經濟學博士,我就跟他說你要想好啊,向前一步走風險是什麼,向後一步是什麼,向左向右又是什麼,站着不動也有風險,我把風險算完告訴你。至於怎麼解決風險?那不是我的事,那是企業家的事。所以一個社會如何能夠造就如此多的密集的企業家,這是深圳內在的東西。
深圳內在的東西還有一條,剛纔海校長也說了,那就是深圳政府和企業的關係邊界劃得很清楚,政府的手不會伸到企業去教怎麼辦企業,這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這張圖是樊綱老師剛纔講的深圳怎麼從低到高的,這是深圳生產過的兩代模擬機,深圳就是從加工裝備開始,然後走自主品牌的模仿,深圳沒有沒模仿過的品牌,深圳人從來不造假,但生產大量的 A 貨。深圳很早就有品牌意識,當年很多人覺得這是山寨版,是 copy 貓、copy 狗。去年是歐美媒體、日本媒體來深圳調研最密集的時候,他們也想知道十年前的 copy 怎麼變成了現在這樣。樊綱剛纔講的很對,全球沒經過模仿時代的,只有一個英國。工業革命剛開始,法國人、德國人都是模仿,英國人就說質次價低的德國貨是不配和英國貨放在一塊賣的,必須要註明 Made in Germany,日本後來也被要求註明 Made in Japan。深圳當年叫“山寨”,深圳自己解嘲說什麼叫山寨,就是 Made in Shenzhen,現在 Made in Shenzhen 走向世界頂級,走向世界頂級的過程就是轉換成長方式的過程。

這個過程我做了一個圖,下邊的線是全國,上邊這條曲線是深圳,然後我做了一個平滑,平滑就可以看到深圳是一路降速的。在深圳的這條曲線中,每十年大概有一個週期。中國人特別怕週期,講週期危機是資本主義,其實我覺得週期是個創新的過程。高潮時大家投資,看到一個風口豬都能飛起來,大家都去投,投了之後就會看到大量飛起來的豬死了,真正的鷹飛起來了。
十年的週期,在深圳表現出產業大量外遷的過程。其中大家可以看到 1984、1985 年,特區工作會批評深圳不搞產業,深圳大衰退一回。
1994 年到 1996 年深圳大衰退,外界變化是 95 年特區政策取消。很多人說深圳特區是政策養大的,其實 1995 年特區辦就沒有了。那一回深圳大衰退還有一個原因是廣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的產業沿着這條高速向北向東莞去了,東莞在五年內取代深圳成爲全國最大的臺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就再也沒有“三來一補”(編者注: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和補償貿易)了,深圳走向模仿,東莞走向“三來一補”。結果東莞在 2008 年開始大規模衰退,“三來一補”在東莞也不能生存了,而深圳已經走到創新階段。
深圳再一次衰退是 2000 年開始到 2003 年,那時廣州成功向重化學工業轉型,成爲中國第三大汽車製造基地,深圳的方向還不明確,那一輪都在討論“深圳被誰拋棄”。
深圳最近一輪轉型可能大家沒有關注到,是 2010 年到 2013 年,深圳 2012 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 4.8%。但深圳當年做了什麼?鼓勵中低端企業外遷,每年外遷的企業超過 8500 家,外遷造成經濟下滑超過 4 個點,深圳經濟當時保持 12% 的增長的時候,它的實質增長率超過 16% 將近 17%。就是因爲這樣一個空間產業轉移的過程,深圳騰籠換鳥。騰籠換鳥本來是當時執政廣東的一位大領導提出之後,很多城市不做,說籠子也騰了,鳥也死了,新的鳥沒來。
我有幾次感覺都很恍惚,我從寶安中心區走寶安大道回市區,進到南山,我不知道哪個是特區、哪個是原來的關內、哪個是原來的關外。8500 家企業走了,寶安就成了一個新的市區,寶安現在成了前海強大的支撐。所以這是一個聚集、擴散、再聚集的過程。從一個空間角度看,它的比較優勢走向轉換的時候是一個不斷的聚集擴散、聚集擴散、聚集擴散。這一過程中深圳的經濟特徵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下面這個表可以說得很清楚。

深圳統計年鑑的數據,1980 年到 2016 年,深圳的勞動力從 15 萬增長到了大概 1000 萬。1980 年,深圳的勞動力三分之一在企業,三分之一在非企業,包括當年的自然村、小鎮,那時候國企員工佔比 83%。深圳國企員工佔比最高的時候是 1990 年代,深圳不是沒搞過大型國企,深圳當年要搞八大企業集團,後來都破產了。深圳大國企都破產的時候,國企員工比例達 91%,從那開始,國企員工比例穩步下降,到 2005 年之後,下降到 20%,再到 9%。企業員工和非企業員工(也就是個體工商戶),佔勞動力的各一半。國企員工現在佔整個企業員工的 9%,佔全社會勞動力的 4.5%。深圳的國企現在就轉換成了這樣一個模式,叫公益性、基礎性和先導性,做好公共服務,做好重大產業的支撐。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深圳企業數的變化,從 1980 年 830 家經過十年到了 2 萬家,再十年之後到了 10 萬家,再十年之後到了 36 萬家,到 2016 年是 150 萬家。最近新普查的數據,深圳活躍納稅企業將近 90 萬家。假如一家企業生產一個產品,深圳就可以生產 90 萬個產品。我們大概知道汽車的製造是民用產品中最複雜的,十萬個零部件,是一個分工極細膩、產業鏈發達、每個分工企業都可以獲得壟斷競爭收益的產業。中國沒有一個城市可以達到這樣的程度,這就是我對深圳的解釋。分工極細,構成極爲複雜的產業鏈關聯的積聚過程,這就是深圳的特徵。

這張圖做了一個美國和印度的比較,印度最好的企業創新對企業的貢獻 0.2,美國最好的企業創新貢獻也不到 0.3,但是美印之間的差別是大量印度企業不創新可以活着,美國企業不創新就不能活。中國大概在印度和美國之間,深圳一定處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我們最近研究了 7000 家深圳企業五年的數據,最後發現深圳樣本企業創新生存水平超過美國的平均水平。我們現在是兩個制度,一個是分工制度,一個是競爭制度,競爭促進了不斷創新。
給大家說一個很典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飛機上看天津的報紙,說天津十年磨一劍,成就了 1000 億的大飛機產業,空客飛機還是裝出來了。我想,深圳五年無人機產業也是 1000 億,這個產業怎麼五年就能冒出來?
首先,深圳有全球最發達的碳纖維應用行業。當年深圳搞無人機的時候我問碳纖維哪兒來的,他們笑話我說我還是管過經濟的副市長,看來你不懂,我說肯定不懂。我告訴你,深圳當年最早給人加工釣魚杆、網球拍、羽毛球拍,再到高爾夫球杆都是碳纖維。深圳做碳纖維做到最高端,一輛自行車賣 24 萬人民幣,比汽車還貴。深圳最高峯時有 10 億隻手機產能,手機外殼就是把碳纖維連起來的,現在華爲手機邊框比三星還窄,那個邊框不是華爲生產的,華爲只創不造,那是比亞迪生產的,王傳福說把這個手機扔出去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我試過真不散。這就代表了材料製造和精密加工能力。還有特種塑料,當年小家電的特種塑料大量遺存,當無人機需要的時候馬上就可以找到。再是電池電控,這是深圳的看家本領。
深圳曾經做了一件事,深圳政府先後投了 5000 萬元研發伺服電機中的磁性材料。機器人是沒有神經的,它靠算法,靠速度。深圳當年根本不知道有無人機這種東西,無人機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智能機器人了,但是深圳還是支持研發成功了伺服電機的磁性材料,最終成就了這個行業。
後來我很好奇爲什麼廣州沒有做成無人機?他們說廣州沒給人做過釣魚杆,廣州也沒做過這麼多貼牌手機,分工鏈在市場化過程中沒有形成過。雖然廣州政府也支持機器人,也支持伺服電機,但和深圳是不一樣的,廣州做機器人是用在汽車產業上,抓鋼板,要求力量很大;深圳的機器人都用在精密儀器上,它力度很小但很精準。所以大疆就具備了在現成產業鏈上做創新的條件。這些將要被淘汰的行業,突然可以給無人機做產業鏈,很多部件,大疆連圖紙都不用畫,汪滔說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給我畫,一個螺絲釘都不用生產,只要想生產就有人給生產,價格又低質量又好。
深圳的做法,總結下來是這樣的,市場是主導,企業是主體,法治是基礎(市場經濟就是合約經濟),政府是保障。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保障,保障合約的履行,政府推動建設發達的法治環境。我在人大工作過,法治不在於立不立法,而是立法技術,爲什麼深圳有這麼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果某個事沒看清楚,那先拿法律當教育文本,出了問題視情節嚴重罰款多少,立法過程是不成熟的,深圳這些年和全國不一樣的是這個地方。

深圳有兩個口號,一個是叫支持非共識創新。
2007 年提出的,當時引起一片譁然,支持非共識創新不就是政府說了算嗎?但現在看這個口號多哲學,要共識了還叫創新嗎?怎麼支持非共識創新,你向政府要錢,一個團隊可以要到一億,先要說清楚五件事,你這個創新的科學原理是什麼?技術從哪個大學出來的?哪個企業做的原樣開發?你和他哪不同?你怎麼確保你成功?沒人知道誰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條件離不開這五個。
深圳還有一個“溼地效應”,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
溼地需要千分之三的鹽份,低了高了溼地都會消亡,政府就保證這塊地千分之三的鹽份,至於進去之後是鳥吃魚還是魚吃蝦、蝦吃蟲,政府不管,那是市場競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選擇,深圳就是按照科學學的辦法來做的,未來重大的科學方向是哪,深圳條件具不具備,要不要發展,這是政府要做的。但深圳政府絕對不會指定,這個領域讓他做,那個領域讓你做。我就經歷過,汪建(華大基因董事長)曾經來找過我,說你們引進了這麼多科學團隊,但是每年發 Nature、Science 論文我們佔 60%,那經費你就直接給我切一塊,別讓我競爭了。我一開始覺得有道理,但是時任深圳市市長許勤說你去問問,他不也是從六七個人搞起來的,爲什麼要欺負別人。所以後來還是乖乖競爭,不競爭就活不了。

聯合國剛剛發佈的報告,橫向從 2005 年到 2015 年,縱向把每一年的產業分成低端、中低端、高端。我們可以看中國的變化,在過去十年我們的中高端產業上升了 2.6 個點,到目前爲止,我們明顯高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國家的邊界。當然,和日韓比、和發達國家比還是有差距,這是我們要轉型的方向。深圳的未來要轉型、要提升,你很出色很成功走到了今天,但是停在今天不會有出路。

同志講了一個“巴斯德象限”,在全國引起熱議。比如技能訓練的是工匠精神,把東西做好,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但工匠能決定中國未來嗎?在深圳就經歷過,曾經有五家做手機屏幕手寫筆的企業,每家做到銷售收入 3 個億以上,曾經控制了全球手寫筆行業的 90%,突然有一天蘋果說我不要手寫筆我要直接手寫,轟然一聲這五家企業就沒了。工匠面對科學,工匠是打不過科學的,所以這個城市要走向科學。
愛迪生模式是另外一種模式,愛迪生沒受過很好的教育,利用現有的科學知識不斷地探索。巴斯德是發現疫苗的人,他受過大學教育,知道發酵,看到因爲發酵可以產生免疫作用,他是偶然發現的,因爲具有成熟的知識得以大規模研發和生產疫苗,這就是大學和科學、大學和產業。這是深圳下一步要做的。當然還有純基礎研究,比如陳景潤,我們現在誰也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破解值多少 GDP,但是他訓練了一代又一代科學家。我們中國到目前爲止很多都是形而下的,不關注形而上的東西,但是我們如果沒有形而上,就不會有科學的突破。

如果循着巴斯德象限再來看深圳,巴斯德是個縱軸,深圳的產業創新是個橫軸。東京-橫濱是世界當之無愧的科學與產業創新中心,它的科學論文居世界前列,全球國際專利申請數最多,所以我們要看到差距。世界大多數名城都位於這個曲線的上方,是以科學爲導向的。我們最著名的是北京,是世界單一城市科學發現最大的,我再多說一句,深圳怎麼走到產業創新今天的,我們去查數據就可以發現,深圳 100 個專利 12 個是和北京合作。北京的科學發現,深圳產業化。北京每 100 個專利 12 個是硅谷來的,深圳每 100 個專利有 8 個是從硅谷來的,結果就形成了世界上沒有的一個罕見現象,跨越 8000 公里的創新三角。有很多人習慣說,深圳“拿來主義”就挺好,爲什麼要辦大學啊?如果不辦大學,所有的科學思想永遠是白紙。

麥肯錫最近做的創新特別是 AI 技術對產業滲透的研究,滲透到旅遊業 55% 將來是 AI 化,汽車今後近 50% 會 AI 化,汽車將是可以行走的超級計算機,這些改變了我們對傳統工業化的看法,傳統工業化從科學發現走到產品要經歷漫長的小試、中試、批量到生產的過程,需要大量的工藝創新和模具製造,現在的生命科學、數字科學會改變這個模式。
深圳從“三來一補”走向模仿,走向製造,走向創新制造,最後要走向科學創新。從科學發現帶動創新,未來深圳周邊會集中大量的製造業,實際上灣區就是城市之間的異質化,現在所有大城市都要做一件事,說製造業是不能離開的,大城市做製造業,中小城市做什麼呢?大城市要引領創新,做創新型製造,不能是做大規模製造,其實這裏面的道理要從空間經濟學講,所有大規模製造創新程度一定是低的,爲什麼呢?它一定要有穩定批量化生產。但是所有大規模製造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單位產出的土地需求彈性釋放,需要大量的土地,所以世界所有大型城市都會集中做創新型製造,走科學創新。

中國的創新人才指數在全球也就排 45,深圳人才薈萃,但是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排 73、一次排 94。我想說的是過去 15 年深圳發生重大變化的是 450 萬企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從 7 年達到了 13 年,15 年達到了別的國家 100 年的變化,但是人才也就如此。
我去年在哈佛待了一個月,在那天天來回走有很大感受,走在波士頓劍橋大街上,論漂亮,比深圳差太多了,但論產業密集是世界頂級,它是全球生物產業最爲密集的一個平方英里,構成了產業結構豐富、價值鏈完整、人才多樣、資金充分、政策穩定,引進了大批創新的生物產業。其實我們知道波士頓劍橋主要是因爲哈佛在,MIT 在,塔夫茨在它邊上,以爲那是一個科教城,它曾經在 100 年的時間是麻省最重要的製造業中心,沉寂了 30 年,走向了生命科學,現在成爲生命科學全球最頂尖的地方。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學,且不說哈佛、MIT、波士頓大學,這幾所大學有三所世界頂級醫學院,兩所世界頂級藥學院,有全球最高端的醫療資源,才帶動了生命科學的集聚,一條街出現了全球 1/3 的生命科學創新公司。

這個城市是這樣的,上邊是 1860 年的劍橋市,下邊是我自己拍的現在的圖片,如果像我們很多城市一樣,沒有多元文化,全部大拆大建,都建成高樓大廈,創新企業是無法生存的,多元化文化可能是極爲重要的。
“都市财经”的新闻页面文章、图片、音频、视频等稿件均为自媒体人、第三方机构发布或转载。如稿件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删除或处理,客服邮箱admin@5iecity.net,稿件内容仅为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不代表本网观点,亦不代表本网站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